好记者讲好故事|丁洋:我与三星堆的双向奔赴
今天的故事,我想从一个我心中的“未解之谜”说起。
2004年刚工作一年的我第一次去三星堆,在青铜馆一楼的大厅里看到了两块近似方形的大石头,这两块石头分别有一个面被打磨的光滑如镜,其中一块还有深深的刻槽,这是明显的切割痕迹。讲解员的声音在耳畔响起,我记忆犹新:“几千年前的古蜀先民,用何种工具、何种智慧,能将这么大一块石头切割打磨得如此精密?这,可能永远是个谜了…”
就在那一刻,作为记者的“雷达”瞬间启动!这不是冰冷的石头,这可是穿越历史的古蜀密码!也就是从那时起,我的“脚力”便一次次奔向三星堆,奔赴那些以生命之火,为沉睡千年的冰冷文物重燃温度的三星堆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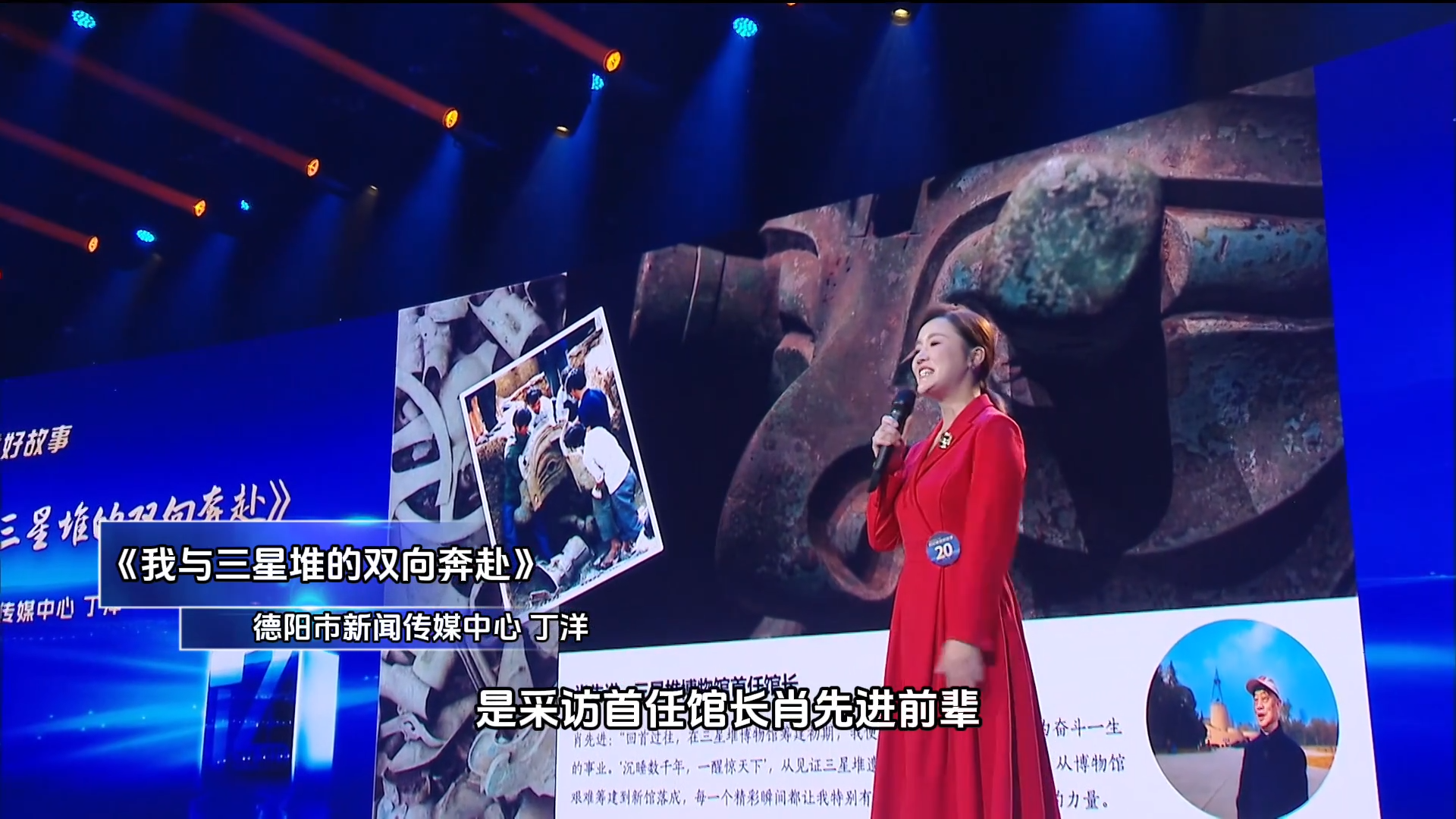
奔赴的起点,是采访首任馆长肖先进前辈,他回忆说,第一眼看到纵目面具时,那种从未见过的造型让他激动不已:“这是祖先留下的文化遗产,建博物馆是保护传承最好的办法”。为了这份使命,他无数次踏上北上的列车,不惧困难,向上争取资金1000万元,敢为天下先贷款2000万元最终建成了到现在看上去都不过时的博物馆。
采访肖先进的故事就像一道闪电击中了我,那份源自血脉的震撼,不仅唤醒了他个人的使命感,更折射出整个民族对根源的敬畏与执着。这份执着,正是对我心中“未解之谜”的现实回应,更坚定了我要用记者之笔揭开谜题的决心。
奔赴的深处,是探访文物修复大师郭汉中,他常说:“修物,实为修心。心静了,手就稳了。”当年修复一号青铜神树,这件近4米高的“世界最大单体青铜文物”出土时,已碎成2000多块残片,完全看不出原貌,没有任何参考。他们只能用“笨办法”,根据残片大小、材质、颜色等特征,一块块比对茬口,推测原本位置。历时6年,2100多个日夜,日复一日的拼接修复,终于让这件3000多年前的瑰宝涅槃重生,成为三星堆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这位技艺超群的大国工匠,不善言辞,甚至多次让我们去采访他的徒弟们,而熟络之后我们发现他还有些幽默,会跟我们讨论他见到的王一博,也会严谨的跟我们交流他文物修复的心路历程。从他办公室出来,跟在他背后,旁边是经他手修复的文物们,这种感觉真的很奇妙,我们就像是无声的在行着注目礼,周围不断擦肩而过的游客没有人认出他是谁。

如果我心中的未解之迷,曾让我困惑于古人的工具;那么今天郭汉中的双手,似乎让我看到了答案——不止是技术,更是那份“择一事、终一生”的执着。记者之路,同样需要这样的匠心。
奔赴的回响,是我工作的20年后。2024年7月23日,当三星堆玉石器“生产车间”找到了的消息传来时,我们采编团队凭借长期的高度新闻敏感,第一时间意识到——这绝非普通发现!三星堆目前没有任何文字记载,主要依靠考古成果来建构相关信息。首次发现手工业作坊,那些散落的石料、半成品、加工工具等都实证了几千年前的古蜀国已拥有复杂精细的社会分工与产业体系!我们在打开这些文物“盲盒”的时候,感受到的是震撼,是惊艳,这也再次告诉了世界中华文明是灿烂辉煌、源远流长的,这追根溯源的文化自信就是我们今天可以平视这个世界的底气所在。而于我而言,心中的未解之谜,终于有了答案。

为了准确传递这一重大考古发现,我们查阅典籍、请教专家、反复推敲。采访三星堆遗址考古工作站副站长许丹阳,他每次都要说出那句:“又来这么快呀?”是啊,车程只有20多分钟的在地优势,让我们可以对三星堆的一切消息做出快速响应。而每一个专业术语的运用,每一次意义深度的挖掘,都是对“脑力”和“笔力”的极限考验。最终我们采写的广播消息《三星堆遗址首次发现手工业作坊》在第二天德阳广播的早高峰节目中顺利播出。
听众给予了热烈的反馈,这些热切的回响充分说明了三星堆在亿万国人心中的份量:三星堆,是中国的三星堆,更是世界的三星堆,它承载着中华民族古老而鲜活的记忆,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实证,是全人类共同珍视的遗产。这个作品获得了2024年四川省新闻奖一等奖,此刻正代表四川在中国新闻奖的舞台接受检阅,无论结果如何,这都不是终点。我与三星堆的双向奔赴仍在继续,用每一次发现、每一次记录、每一次讲述,去奔赴历史的深处,奔赴那连接过去与未来、中国与世界的文明长河!

此刻,我仿佛又看到了那两块沉默的巨石,它们光滑的切面,曾是一个“未解之谜”,而郭汉中的巧手、肖先进的改革雄心、手工业作坊的发现和我们的报道共同点亮了这个谜底。
202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川视察,在三星堆博物馆新馆,他说:“三星堆遗址考古成果在世界上是叫得响的……”,他期待着更长的中华文明的发现发掘。
未来,我们将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继续讲好三星堆的故事,讲好中国故事,用手中的笔和镜头去解读一个又一个时代的“未解之谜”,去书写一个又一个激动人心的“中国答案”。
经过激烈角逐,德阳市新闻传媒中心记者丁洋获得二等奖。


评论